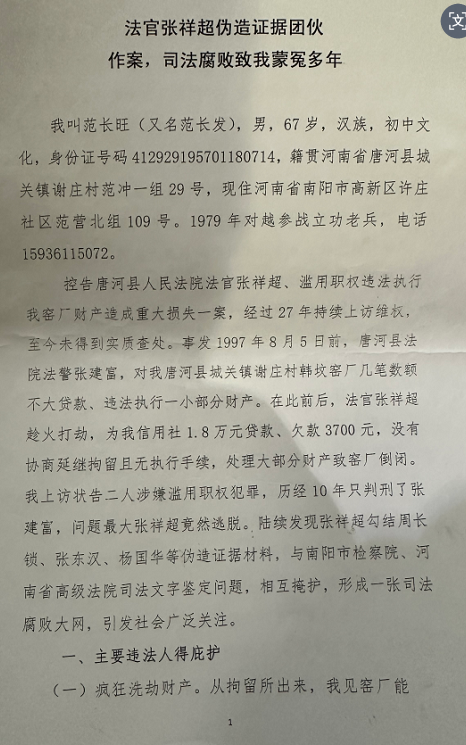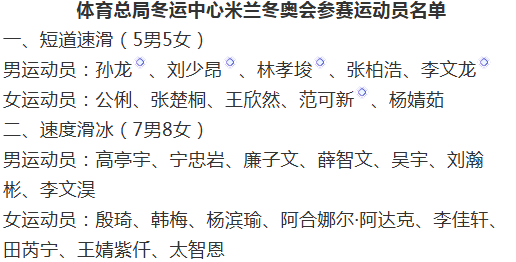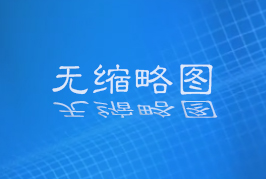先学会道歉赔偿,再来谈尊重法治
举国关注的聂树斌案又有了新消息。日前,聂树斌的家属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,要求赔偿1391万元。
这1391万元赔偿金大致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是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等等,约为191万,另一部分是精神赔偿金,约为1200万,后者占了大头。如果不是聂树斌案轰动全国,举国关注,不知道聂家还敢不敢提出这么高的精神赔偿。
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此前类似案件的赔偿连这个数字的零头都不到。1998年,湖北省京山县人佘祥林因涉嫌杀害妻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,但2005年3月,其“亡妻”突然出现,佘祥林被无罪释放,他向国家提出赔偿1000万,但最后到手是多少呢?70万。1999年,河南村民赵作海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被判处死刑,缓刑2年。2010年4月,河南省高院认定赵作海案系一起错案,服刑11年的赵作海沉冤得雪,赔了多少呢?65万。
《国家赔偿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:造成死亡的,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,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。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,还应当支付生活费。聂树斌家属提出国家赔偿中的第一部分,就是以此为依据来计算的。至于精神赔偿,2014年,最高法院曾经出台了一个意见,规定精神赔偿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、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%,若沿用这个标准,聂树斌的家人可能获得的精神赔偿金很难超过70万,距离1200万还有遥远的距离。
在许多国家,精神赔偿金的额度是很惊人的。比如美国一名男子在16岁时被控性侵了15岁的同学,尽管DNA证明他无罪,却仍遭判刑入狱,还因此坐了15年的牢。重获自由后,他状告法院并胜诉,获得超过4100万美元,约合2.5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……要扳起手指一项项算误工费、医药费等等,这些赔偿金显然高得离谱,但如果从精神赔偿的角度来看,却又高得有理。
聂树斌案之所以备受关注,是因为人们希望这起案件能够改变中国法治中某些看似合理、无比坚硬却又未必经得起推敲的东西,没错,这里的核心正是“改变”。纠正聂树斌案的错判如此,在国家赔偿方面也是如此。
当然,我们说要依法行事,不能因为某一起案件被媒体曝光公众关注,就多赔一点,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“非法治”。但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面对“改变”呢?今年5月,海南省高院支付坐了23年冤狱的陈满国家赔偿金共计275万余元,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90万元,为人身自由赔偿金的50%,超过了法定的35%的比例——对,这就是一种“改变”。那么,聂树斌案又会有怎样的“改变”呢?
人们希望看到的“改变”当然不仅限于此。现行的《国家赔偿法》本身是否也需要重新考量和审视,并予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是个问题。正如聂树斌案的误判和反转同法治有关又无关一样,人们期待的是一种真正基于法治精神、不为各种人为因素所左右的公正稳定的标准。
进而言之,借由聂树斌案的赔偿,我们还应该对国家赔偿这一严肃的问题予以更全面、更系统的观照和思考。比如曾经波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,以及毒胶囊事件等等,它们危及的人群何止千万,但那些喝过毒奶粉、吃过药丸的人们,又得到了怎样的赔偿?这些年来,我们有太多该认的错没认,该赔的钱没赔。纠正一起冤案要花二十多年,法律被冷落一旁;该赔钱的时候又显得无比精细,处处拿出法律条文来抠。这种法治的似有若无,我们领教得太多,纠结得太多。要谈尊重法治,还是先从道歉赔偿这样的“小事”做起吧。(彭健)